?

鹵簿鐘上祥云蔚繚的宣德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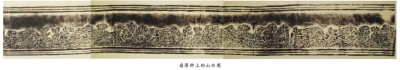
鹵簿鐘此番在博物館里是裸展,雖然設了一個矮圍欄,但絲毫無礙探身細看,因此每個細節都歷歷在目,鑄在鐘上的“千里江山圖”也是如此。不過既有《鹵簿鐘的年代研究》在先,則仍以照引為宜:“鹵簿鐘身飾紋第四層,凸鑄一條橫繞鐘身一周的山水紋帶。這條飾紋帶,是由三段相同的畫面相連結,構成一幅氣勢磅礴,山勢連綿的山水圖卷。就其畫面內容,擇其一段,則可窺其全貌。畫面取景作橫卷式,以六座高山前后交錯布列,成為整個畫面的中心。六座高山分前后兩排,形成一條由右向左的狹長山谷,由于前排三山的遮擋,在畫面上形成了三個空間:第一個空間,右下角有一行者趕著毛驢,將從溪上小橋走過,沿著前方的夾谷山路而去。在其右邊的山谷里,一勞作者似荷鋤而歸。在其前上方的山腳下,有一茅屋隱約可見。第二個空間,是由左面相連的三山和左面一山相對,中間出現一條斜長的
山谷,溪水沿谷底而流。左上方,有一亭式建筑倚立于左三山的山坳之前。右山腳下的溪水邊,停泊著一小木舟,景象異常恬靜。第三個空間,則是第二個空間左三山向左的延續,在畫面最左面的山坳間,亦有兩座茅屋隱現。有的茅屋頂上挑著一面小旗,是為酒肆的標志。從整個畫面看,近景是峰巒迭嶂,遠景則是山勢連綿。樹木、溪流、小橋、木舟、茅屋、酒肆等點綴其間。”“就鹵簿鐘飾紋帶所表現的山水題材來說,也具有北宋繪畫中山水長卷的時代特征。”
中秋節前,曾兩番進“宮”近距離觀看《千里江山圖》;不意在此又與北宋鹵簿鐘上的“千里江山圖”相遇,一先一后同為政和年間物,而俱與徽宗及蔡京相關,頭腦里映像的疊加幾乎不可避免。鹵簿鐘上的山水圖,大到重崗疊嶂聯絡映帶的整體布局,小到曲澗幽溪的景物點綴,諸如溪橋、泊舟、亭閣、茅舍、勞人,更有山勢及山峰肌理的表現手法,雖然一為繪制,一為鑄造,精粗有異,繁簡有別,但二者的相似,實在一目了然,甚或要說后者是前者的簡易版,乃至前者竟是粉本亦未可知。看展廳墻壁上鹵簿鐘的拓本照片,便更可會得山水長卷的意味,且以它的循環往復而頗有江山無盡的效果。銅鐘皇家制作的性質,是沒有疑義的。《鹵簿鐘的年代研究》中說道,“若按鹵簿鐘飾紋中所表現的中心,皇宮大內的宣德門,當是作為北宋王朝的象征。而宣德樓又在政和八年改建,因此可以設想鹵簿鐘是為了在改建后的宣德樓上懸掛,作為北宋王朝的朝鐘而鑄造的”。如果這一推論可以成立,那么它與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正可相互發明。王希孟《千里江山圖》是宋代青綠山水之唯一,鹵簿鐘上如此氣勢的“千里江山圖”也是銅鐘紋飾之唯一,兩件不同材質的作品,卻有諸多偶然的關連———徽宗與蔡京,政和三年(《千里江山圖》隔水黃綾蔡京題識起首即云“政和三年閏四月八日賜”)與政和八年,相關的人物以及耐人尋味的時間節點,似可構成前后相銜的兩段歷史敘事而成為畫作與銅鐘共同的背景,共同的政治寓意或也隱然在其中。
(作者:揚之水 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