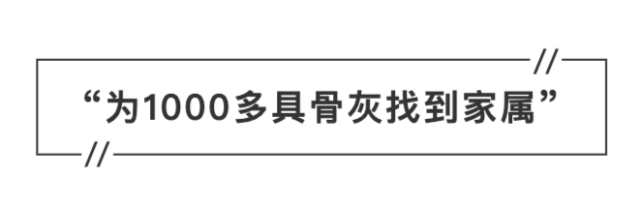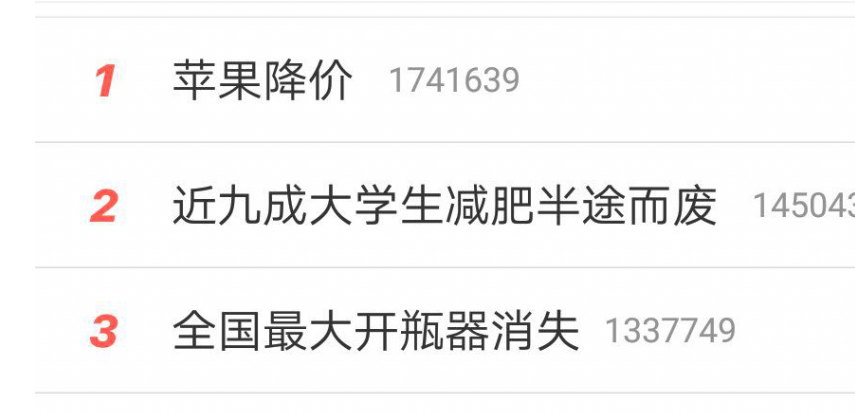深圳90后殯葬師:送逝者最后一程的擺渡人
南方+2019年4月3日訊 幾乎每一位在深圳離世的逝者,都要經由位于龍崗丹竹頭的深圳市唯一的一所殯儀館,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來到深圳殯儀館,坐著邱陽(化名)開的電瓶車往墓園走,山間的墓碑如同一個個神龕,背后閃著夕陽散漫的光。
邱陽生于1990年,即使不算在學校那3年,他做殯葬行業也有7年了。當初不顧爺爺反對,執意要學殯葬專業的他,如今已在深圳結了婚、安了家。
在深圳這5年,邱陽只有兩個春節回了老家。“我熱愛這份工作,現在很穩定,父母也漸漸看開了。”說這話時,他的拇指和食指夾著煙,升騰的煙霧如同陽光下燃燒的紙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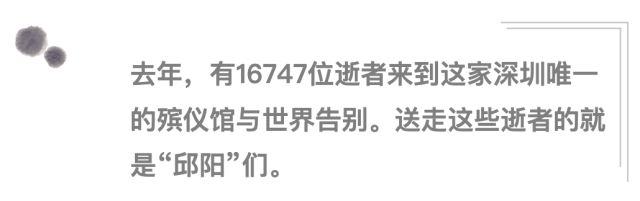
7年來,邱陽從事過遺體接運、防腐、化妝、殯葬禮儀、骨灰寄存、檔案管理……這差不多是殯葬的全環節。
“人總有生老病死,這最后一步是我們送走的。”在邱陽心里,殯葬師就是人間與天堂的擺渡人。

邱陽第一次接觸遺體是在2009年的冬天,那是他讀大學的第一個寒假、第一份實習。“當時師傅沒要我化妝,也沒有出車,就是簡簡單單地將遺體從禮堂推到火化車間。”
在當地,這一環節沒有蓋棺蓋的習俗。“車的高度略低,我彎著腰,距離遺體的臉只有15公分的樣子。”邱陽說,白天還沒覺得什么,當晚就做了噩夢。
往后的日子里,邱陽每天都需要喝一點酒,暈乎乎地才能入睡。直到實習快結束時,他才接受了這個“距離”,“我那時覺得,‘死’是一件很有神秘感的事。”
邱陽畢業于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是目前國內僅有的幾所開辦殯葬學專業院校中,最好的一所。
但20余年來,該校也僅僅為中國的殯葬行業輸送了5000余名畢業生。
“中國那么多殯儀館,撒下去都濺不起水花的。”
在學校里,邱陽經歷過殯葬服務學、殯葬禮儀、遺體防腐、油彩、色彩學、火化機維修、殯葬心理學等一系列專業訓練。但在殯葬這個行當里,實操往往比理論更重要。以殯葬心理學為例,邱陽說,“難的是對自我心理的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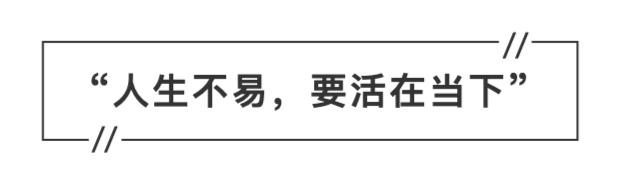
到深圳后不久的一次重要任務,至今讓邱陽難忘。
國內某市一艘載滿乘客的客輪在長江中游水域突遇罕見強對流天氣后沉沒,有大量乘客落水遇難。邱陽作為廣東省民政廳殯葬救援隊成員,趕赴事發地善后處理,進行“遺體整理”。
“那是我第一次密集接觸那么多遺體,在三天時間里不斷對遺體進行清洗、打包。”邱陽說。時間緊任務重,三天時間里,救援隊兩班倒,每天不斷重復著相同的動作。“在船體剛剛扶正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是24小時堅守。”
“天氣很熱,累了,我們就席地而坐,靠墻睡一會兒。”即便如此,救援隊也不會解開防護服、口罩和護目鏡。“尸體腐臭很嚴重,回到休息的地方后,感覺氣味已經透過了防護服。”
說起這段經歷時,邱陽很平靜,他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歷練,感覺自己對生死看得更明白了。“人生不易,要活在當下。”
2016年年初,邱陽調崗到骨灰寄存。當時,深圳市殯儀館正在進行改擴建工程,舊骨灰寄存室與舊墓廊都需拆除,歷年來積存的5000多具骨灰需要經辦人前來搬遷。
“我每天要打一百多個電話,但只有不到30%找得到經辦人。”邱陽說,無論是誰聽說是殯儀館的電話,都會覺得晦氣。“那也要打,一旦能接通,就意味著有一半概率能聯系到家屬,最起碼能有直接的對話。”
經過邱陽們的努力,5000多具骨灰中有1000多具由家屬前來親手遷移,余下的由殯儀館依照合法程序代為遷移。在這些骨灰里,比較早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家屬留下的聯絡方式還是尋呼機號碼。
對于“被遺棄”的骨灰,“雖然找不到家屬,我們也不能私自處理掉。”邱陽說,如果有一天家屬過來找不到骨灰,那對他們會是比較嚴重的打擊。
“也有聯絡到家屬了,卻無法來搬。”譬如說,通過老號碼輾轉多人聯絡到的逝者子女,已經移民國外,“他們會遠程傳真委托書和身份證明過來。”
有一對夫妻出具了委托書后,卻來到了現場,看著工作人員遷移骨灰。“因為風俗問題”,骨灰盒里是他們的孩子,父母不能抱或端孩子的骨灰。
人們對“殯儀館”的排斥與對“死亡”的忌諱密切相關。作為殯葬師,邱陽深有體會。前不久有家屬來取骨灰時,希望拿走去世親人的所有檔案,因為里面也有這位家屬的簽字,他不希望自己的任何痕跡在殯儀館留存。邱陽苦笑道:“我只能跟他們講,這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許的。”
“我們這個行業社會地位確實不高,我出門也不說自己是殯儀館的。”但內心里,邱陽卻認為,生老病死都是人生的過程,能為一個如此重要的時刻服務,是很高尚的,“殯葬師是人間與天堂的擺渡人。”
“不用那么沉重,不需要太悲傷,活著已經足夠幸運了,人就應該積極地、充滿正能量地活著。”邱陽說。
【視頻】劉玳杞 胡佩瑤 何雪峰
【剪輯】劉玳杞
【記者】何雪峰
【統籌】張瑋
【出品】南方+深圳新媒體產品實驗室